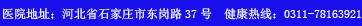食物是文化的一部分,中西方都是平等的
2022/11/19 来源:不详在一些文化当中,食不厌精和食不厌多这两套标准在贵族显要之间相持不下。有些精英分子(有时是高消费精英阶级中彼此竞争的各派人士)设法以细致之美挑战量大即是美的信念。他们另有主张,谴责没有节制的饮食是野蛮行径,赞扬简单朴实才是高尚行为。孔子的饮食主张就代表君子之道。孔子曾表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并不违背简朴的原则;在这些方面将就行事反而是野蛮行径。不过,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不撤姜食,不多食。孟子谴责富人无视穷人的匮乏,放纵无度;他表示养心莫善于寡欲。食量小是佛性的体现。穆斯林认为,人们可以吃大地上所有合法而佳美的食物,但是在阿拉伯宫廷烹饪中,简朴的沙漠菜式与奢华的城市佳肴两相对抗,形成极具创意的张力。
婆罗门对食物漠不关心,就如同戈德博尔(Godbole)教授在一篇讲印度的文章中所言,他们仿佛是意外地遇到了食物。毕达哥拉斯乐于禁食;节制是斯多葛学派的美德,希腊的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认为,吃和交媾一样,皆应偶尔为之。在耶稣的圈子里,五饼二鱼就是丰富的飨宴。虽然上述先圣先贤似乎并未对上流社会的饮食习惯造成立竿见影的影响,然而凡是受其影响的社会,禁食似乎逐渐成为精致的代名词。
影响所及,部分地助长了上流社会饮食的另一项典型悖论,即奢侈的权利只有在被主动放弃之时,才象征着真正的贵族。真正的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传闻中恺撒是节俭的典范,他的后继者吃得都比他多,这就显示了他们比不上他。他爱吃平民百姓的食物,比如粗面包、手压的奶酪、次等的无花果。他往往在马背上匆匆进食,而不愿花时间好好吃一顿饭。他号称比安息日的犹太人更严格守斋,据称他餐后不喝酒,改食黄瓜和酸苹果以助消化。成吉思汗从不被他征服之地的文化所诱惑,从不因而偏离北方的严苛生活。领导苏格兰人抗英的美王子查理(BonniePrinceCharlie)深受爱戴,因为他可以在4分钟内打胜仗,在5分钟内吃完晚餐。据说拿破仑爱吃薯条和洋葱,他是真正喜欢呢,还是假称喜欢,借以凸显他乃平民君主,这就不得而知了。
有三种方法可以调和节俭和过度这两个概念。第一种就是精挑细选奇珍异食;食物本身就够引人注目,故量虽少却足以彰显贵气。第二种是精心调制数量不多的食物。这两种方法助长了现在所谓的精食主义(foodism)——用尤维纳利斯(Juvenal)的话说,就是一眼便可辨明海胆的美食鉴赏功夫,[插图]这使得饮食变得深奥了。最后一种方法是制定各种奇特的礼仪,只有精挑细选、受过训练的人才懂得,这使得食者不必注意该吃哪些奇特的食物、端上桌的分量有多少或者该用什么特别的手法调制。要紧的是,该怎么用餐。
古罗马皇帝赫利奥加巴卢斯(Heliogabalus)因采用第一种方法而恶名昭彰。他是放纵无度的化身。他放纵并非由于贪吃(虽然他经常被这样指责),也不是因为他明显地热爱奢华。他真正追求的是猎奇,迷恋前所未见的奇特事物。他想要活在奇异即常态的世界,他所嗜好的是烹饪的超现实主义。他把挥霍变成艺术。他用鹅肝喂狗,请客人吃镶了金边的豌豆、嵌着玛瑙的扁豆、拌了琥珀的豆子和用珍珠点缀的鱼。
据说他创制了一道用只鸵鸟的头做的菜。用餐时,他重视排场装饰甚过味道,重戏剧手法甚过烹饪技术。他吩咐手下把鱼摆在蓝色的酱汁中,以模仿海洋。在古罗马皇帝中,他唯一的对手是维特里乌斯(Vitellius),后者设计了智能之盾,上面拼满了海鲈肝、八目鳗、鱼白,还有野鸡、孔雀脑和火烈鸟舌。[插图]当然,对于这些餐宴的描述,我们应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巴洛克式宴席可能会令罗马人作呕,因此有关上述场面的描写,通常来自清心寡欲的批评家,他们的本意当然就是要让读者感到反胃。
端上反季菜肴也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效果,这也是高阶人士饮食的特色,因其违反自然而带有英雄气概。17世纪一位大厨假惺惺地写道:若我有时在1月或2月……订购一些起先看来不合季节的东西,比如芦笋、朝鲜蓟和豌豆,请别惊异。为费拉拉的贡萨加(GonzagaofFerrara)担任家厨的巴尔托洛梅奥·斯特凡尼(BartolomeoStefani)写了一本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食谱,故意要吓吓购买这本书的资产阶级人士,他所列的菜品只有荷包满满、家有良驹的人才享受得起,对此他颇为自豪。某年11月,在招待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的宴会上,他上的头一道菜是白酒草莓。[插图]这道菜令人惊喜,又带有某种潇洒而优雅的气质。在文艺复兴礼敬节制的风气尚未传入厨房以前,厨师可以理直气壮推出令人惊喜的炫目菜式。年在曼图亚公爵的婚宴上,有做成镀金狮子模样的鹿肉饼、弄成黑鹰傲然挺立模样的馅饼、看来栩栩如生的野鸡肉饼。孔雀用孔雀毛来装饰,点缀着缎带,并使其直立,像活生生的一样,点燃鸟嘴中的填充香料,香气四溢,鸟腿之间还放了情诗笺。还有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以及独角兽的雕塑,是用杏仁蛋白糖塑成的。
不过,即便是此等场面,比起多年前的一场西方有史以来最豪奢的宴会,也是小巫见大巫。年2月17日在里尔,勃艮第的善良者腓力(PhiliptheGood)在宴会上发表野鸡誓言,强迫在座宾客立下十字军誓约,颇像是现代的募款者在慈善宴会中被强索捐款。据一位宾客叙述:桌上搭了小礼拜堂,内有唱诗班,有个大馅饼,上面站满了长笛手,还有座角楼,自内传出风琴声和其他乐声。喇叭手骑在人扮的马和大象上,替公爵上菜。接着有个少年骑着匹白色公鹿登场,少年歌声悠扬动听,随着鹿的脚步,少年歌声益发高昂,然后来了头大象……扛着一座城堡,里面端坐着神圣的基督徒代表,他代表所有遭受土耳其人迫害的基督徒申冤,令人动容。[插图]宴会作为表演的传统仍在延续。金融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Buchanan)和钻石大王布雷迪(他以能在晚餐前吃上四打牡蛎而闻名)都是传奇的马背宴会的座上宾,该宴会在路易斯·谢里(LouisSherry)的纽约餐厅中举行,骑手和他们的马在那里甚至能坐电梯到三楼的舞厅。
对奇异食物、餐桌奇观和桌边余兴表演的喜好,并不只是粗俗的品位。中世纪的黑鸫馅饼、现代会蹦出跳舞女郎的告别单身派对蛋糕、惊奇鸡(pollosorpresa)、惊奇炸弹(bombesurprise),人们对凡此种种惊奇食物的爱好,都是把烹饪当成戏剧表演的例证。其中当然也有知性的一面。惊奇有如谜题,引人苦思,经过伪装的食物则是知识分子游戏的素材。在教育乃精英特权的社会,这使得惊奇食物成为上流阶级的饮食。古时的京都便有种习俗,宴席上的来宾常常竞相猜测他们吃下去的是什么东西,[插图]就像今天在餐桌上猜测葡萄酒的名称和年份一样。多萝西·L.塞耶斯把后者作为神秘故事的关键。她笔下的彼得·温姆西勋爵(LordPeterWimsey)在与他的冒名顶替者的竞争中,凭借其准确无误的嗅觉、味觉和品酒知识证明了他的身份。
不过,在既不过量却又能凸显与众不同这一方面,戏剧化食物仍有不尽完善之处:这类食物太炫目了,因此永远无法显得朴实。说不定有个更好的方法就是,不求量多而强调烹饪技术,设法创制烹调耗时的菜肴,以显现贵族阶级的闲逸。这也是用食物来区分社会等级的方法之一,就像其他所有的方法,支持这种方法的人辩称它是文明传统的一个阶段。若古(Jaucourt)在启蒙运动圣经《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有关烹调的词条中说:厨艺几乎就仅由菜肴的调味所组成,所有文明国家皆是如此……大多数调味料有害健康……但大体而论,必须承认只有野蛮人才会满足于纯粹的天然食物,就这么吃,不加调味料。除了调味料,最极致也最能显现精心料理功夫的就是酱汁,这也是一种伪装虚饰的方法。
在现代烹调中,酱汁一般用来加强味道或提味;但它仍是面具,遮盖了它所烘托的食物的味道。原味派烹饪(plain-cookingschool)嘲弄使用酱汁是遮掩低劣食材的办法。实际上,酱汁极可能是用来烘托最上等的食物,因其正是宫廷烹饪的特色。熬酱汁需有大量材料并提炼浓缩,因此费钱又费事。酱汁往往有印象主义式的魔力,它产生的化学反应能使得食材出现令人意外的转变,比如蛋黄酱和蒜泥蛋黄酱,原不过是加了橄榄油以后乳化的蛋黄或大蒜;还有咖喱,它使水牛脂尝起来不油腻;泰国鱼露则将腐鱼化为不可或缺的调味料。调制酱汁属于专业技术领域,尤其是比较复杂的酱汁。因为要想制成好的酱汁,必须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见多识广的判断力。酱汁的做法繁复难记,从而激发了烹饪的学术传统;酱汁的食谱必须用笔记下,遂成为能读写之人的特权。世上最古老的食谱据说就是酱汁的做法,那是公元前2千纪晚期中国周朝的一个腌汁食谱:把生鲤片浸泡在萝卜、姜、葱、紫苏、花椒和两耳草混合的腌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