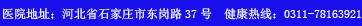张青春扁豆的清欢滋味
2022/7/22 来源:不详扁豆的清欢味道张芳华
在城郊路边的瓦砾堆傍边,我惊叹地发觉一架扁豆花。扁豆架紧挨着人行道,背面是两间老旧的民房,藤蔓攀附墙根爬上去,笼罩一大片屋瓦。细密的绿叶丛里,一串串白色的、紫色的扁豆花,有的高挑出来,好似胡蝶振翅欲飞;有的爬上房坡,趁势捉住瓦片一起进取延长;有的垂下,如绿钩倒挂;有的羞羞答答,藏匿在肥绿的叶片间,兀自开着,芳香而妖艳。黄昏的秋风里,三五只蜜蜂嗡嗡嘤嘤,恋花抱蕊,喧哗得很。这个时分,一个老妪从屋子背面逼仄的天井里走出来,掂一只小马扎,坐在扁豆架旁,戴上老花镜择菜、剥毛豆。在她的身边,一只黄狗摇着尾巴这边转转那里闻闻,一眨眼钻进扁豆架下。我悄悄地立足寓目,老妪好似忽地望见了我,便咧开枯瘠的嘴唇呵呵地笑,嘴角和眉梢儿遮掩不住一脸的慈悲、安全和宽大,像极了乡村梓里的老母亲。
乡村梓里,过日子的人家老是离不开扁豆。明亮节令,房前屋后、沟边河沿,顺手挖穴丢下几粒扁豆种子,不出十天半月,便开展三两片嫩叶。在豆苗根部撒一把草木灰做肥料,豆苗很快叶绿苗壮。炎天萌生一蓬新绿,扁豆架是一个乘凉的好去处,严实、兴隆,极富诗情画意。大人们忙碌一天,在扁豆架下用膳,聊家长里短、说古今闲话,是很适意的。夜已深,和风习习、蟋蟀声声,儿童们照旧不愿回屋安睡。这个时分,母亲就会奇妙兮兮地说《聊斋志异》的鬼故事,吓得咱们捧首鼠窜,回屋蒙上被子,敛色屏气,好似妖妖怪魅就站在床边。立秋以后是一架白茫茫或紫莹莹的花朵,一架弯似娥眉的扁豆。
扁豆,亦名藕豆、豆角、刀豆、鹊豆、沿篱豆、皮扁豆、白扁豆、火镰扁豆等,有点像旧时戏文里丫鬟的芳名。李时珍《本草提纲》提到:“藊本做扁,荚形扁也。”“藊”字取其豆荚扁平之象形。咱们那地点,可能因其弯弯的、长而扁平,好似纯洁女郎的蛾眉,便抽象地称之为“眉豆”。
扁豆大体在秦汉时代由印度传入我国。成书于西华文帝时代的《大荒纪闻》中记录了一种豆子:“身毒有荚豆,扁薄类豚耳。”身毒,指印度。虽未确认其为扁豆,但时至昔日豫东村庄仍有一种叫“猪耳朵”的扁豆种类,大体能够坚信这类所谓的“荚豆”便是扁豆。陶弘景《名医别录》第一次确凿地提到:“扁豆味甘,微温。主和中,下气。叶主治霍乱,吐下不只。”扁豆最先投入我国,是被当药用来治病的。
小时分,我总爱靠近小小的扁豆花,闻到一丝淡淡的幽香。独特是正午,扁豆花的芬芳蒸腾起来,淡淡的幽香里带一点儿淡淡的甜味,我的心会一下子静下来。偶然,我禁不住,寂静地掐下三两朵淡紫色的小花,吊在本人的床前,好似紫色的风铃,时常常看上一眼,充足无穷遐思。这个时分,母亲发觉了,便责怪道:“一朵花,即是一个眉豆。这是养人的菜呀!”
扁豆有多种吃法,凉拌,炒肉,扁豆焖面,而我最喜好的仍是凉拌和清炒扁豆丝。我上三年级的时分,母亲从临盆队里放工回来,急急促地三步并做两步跨到院墙外边,摘下一竹篮扁豆,尔后择菜,淘洗洁净,滚水里焯一下,捞起,凉水过一遍,一把一把,团在手心,挤掉水份,切碎,淋以蒜泥、陈醋、小磨香油,吃起来平淡而爽口。若清炒扁豆,小炒锅放入适当净水烧开,悄悄放入扁豆丝,三五分钟后捞出,过凉水,控干,备用。蒜瓣切成片或末儿。葱花、姜末儿、辣椒段备用。锅内放入适当素油,油热以后放入蒜末,煸出香味,再把扁豆丝放入爆炒。扁豆焯水,一炒就熟,再加之蒜末的幽香、椒段的辣香与食盐的微咸,响亮适口,味道绵长。
扁豆吃不完,母亲除了送给邻居邻人一些,还把扁豆角焯熟、晒干,装入土布紫花布袋里,珍惜起来,等过冬时,赶集割未几的猪肉,上笼,蒸扣碗。干扁豆与肉蒸,筋而不柴,俗称“有嚼头儿”,鲜美中有一重干菜香,人们就着高粱面窝窝头,吃得津津隽永。暖老温贫的扁豆,能给通俗百姓充饥,也能抚慰农户的清苦,使我渡过了清苦而无忧的少年时间。
扁豆入诗文,古今多有佳句。明朝王伯稠《凉生豆花》写道:“豆花初放晚凉凄,碧叶阴中络纬啼。贪与邻翁棚底话,不知初月照清溪。”夜凉如水,豆棚之下和邻家老者闲话长坐,悄然无声中月色已把溪水都照亮,夜曾经很深了。短短四句,充足诗情画意,让品质味不尽,扁豆既有陶渊明的隐士遗风,也有苏东坡的清欢味道。而清朝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中,对眉豆有一段文华动人的记叙:“观其矮棚浮绿,纤蔓萦红,麂眼临溪,蛩声在户。新苞总角,弯荚学眉;万景澄澈,一芳摇漾……秋郊四眄,此焉情极。”文句漂亮,谈话灵便,把眉豆花写得走神入化,直教人生出几分爱惜。汪曾祺在《食豆饮水斋闲笔》中也写道:“暑尽天凉,月色如水,听纺织娘在扁豆架下沙沙振羽,至厚情趣。”秋日的味道就在这些花朵里、秋虫里。其余,他在《食豆饮水斋闲笔》中所谓的“棍儿扁豆”,本来不是扁豆,而是四时豆。四时豆,学名菜豆,亦称云豆,浙江人称明亮豆,四川人称四时豆,朔方人称眉豆。
扁豆也入画,有不少名家喜好以之做短文。白石老翁也爱画扁豆,寥寥数笔,扁豆花红红白白,扁豆荚随风摇荡,再加之一只蚂蚱,可能蟋蟀,可能小鸟,满纸秋色喜人。“文明大革新”期间,汪曾祺情况困顿,一家五口住在一个拥堵霉湿的大杂院。他用破缸种了一架扁豆,扁豆藤疯长,爬墙过壁,遮住了前屋人家的窗户。秋日,扁豆长成了,他摘了几斤送给人家。对方说,能不能送他一副扁豆花的画。汪曾祺急速准许。后来,这幅画向来挂在这户人家的显眼处。
回顾中的梓里,村路弯弯、流水潺潺,家家户户泥墙瓦舍,竹篱挨住竹篱,爬满红白白的扁豆花。若悠闲走在乡下巷子上,好似走进扁豆花的长廊,内心充足了暖和。今朝,家家户户早已没有了竹篱,二层小楼星罗棋布,院墙也建得越来越高,再也见不到那种画面了。
本文配图和文字以及音频未讲授做家的敬请做家联络